黨建 | 黨對中國革命基本問題的探索(二)
日期:2021-07-30 14:31:07來源:未知瀏覽次數:0

爭取無產階級領導權問題
黨的四大前,共產黨人已在不同程度上對無產階級領導權問題進行過探討。四大明確提出了無產階級在民主革命中的領導權問題,但對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爭奪領導權的嚴重性和實現無產階級領導權的途徑還缺乏認識。在五卅運動中,中國工人階級又一次充分顯示了自己的力量,而資產階級在五卅運動中卻充分表現出它的兩面性。隨后,國民黨右派又加緊了對革命勢力的進攻。這些事實,使共產黨人進一步認識到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爭奪領導權的重要性。
陳獨秀
“五卅運動固然是各階級聯合的民族斗爭,然而實際上和帝國主義直接抗爭的,乃是上海、香港、漢口、九江、南京、青島、天津、焦作等處的罷工工人,其他各界人士不過是工人階級之聲援罷了”,因而,“我們固然不能夸大的說中國工人已是現時中國革命之唯一的勢力,而卻不能不承認他是一種重要的可靠的力量”;而資產階級“那妥協猶豫的態度,已足夠帝國主義者及軍閥乘虛而入了”。
劉少奇
“工人階級在‘五卅’反帝國主義運動中犧牲為最大,主張最為急進,奮斗最能堅持,力量亦表現得非常偉大。在各種奮斗事實中,足以證明工人階級在國民革命運動中之領導地位,是確鑿不移的。”“中國資產階級本來受帝國主義與軍閥壓迫,他們有參加國民革命之可能,但資產階級參加國民革命終究是妥協的,不能徹底的。
瞿秋白
五卅運動中資產階級軟弱退讓,使罷工斗爭遭受挫折,資產階級的妥協性和小資產階級的猶豫畏怯,足以“證明無產階級在國民革命中取得指導權之必要”。
在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爭奪領導權的問題上,共產黨人提出一個重要觀點:這種爭奪不能局限在群眾運動方面,還應當重視政權問題。
鄧中夏
“我們對于國民革命,即為了取得政權而參加的”,但是“政權不是從天外飛到我們工人手中的,是要我們從實際政治斗爭中去一點一滴的以至于全部的取得”。他特別強調:“政權我們不取,資產階級會去取的”;只有無產階級在政治上的地位與勢力日見增長與鞏固,才能“防范資產階級在革命中之妥協軟化,并制止其在革命后之政權獨攬”,給將來建立工人政府“預為準備”。
周恩來
“工人是國民革命的領袖,要領導農人兵士而為工農兵的大聯合,共同來打倒帝國主義。”
1926年7月,在國民黨新老右派加緊反共的嚴峻形勢下,黨的中央執委會擴大會議在《中國共產黨與國民黨關系問題議決案》中指出:“我們在國民革命中的策略,應當更加明確規定:一方面我們的黨應當更加加緊在政治上表現自己的獨立,確立自己在工人及多數農民中的勢力,取得革命化的一般民眾中的政治影響;別方面組織這些小資產階級的革命潮流而集合之于國民黨,以充實其左翼,更加以無產階級及農民的群眾革命力量影響國民黨,——這樣去和左派國民黨結合強大的斗爭聯盟,以與資產階級爭國民運動的指導。如此才能保證無產階級政黨爭取國民革命的領導權。”這些論述說明,在事實的教育下,中國共產黨人對無產階級領導權的認識比過去有所深化,已經從一般地談論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爭奪領導權,進到如何在國民黨內部取得政治指導的地位。
武裝斗爭問題
對作為中國革命主要斗爭形式的武裝斗爭問題,這時黨在認識上也有新的進步。此前,共產黨人批評國民黨專做軍事工作而忽視民眾運動,但自己卻往往專做民眾運動而忽視軍事工作。在統一廣東革命根據地的過程中,黨開始注重開展兵運工作和加強對軍閥部隊的宣傳工作,以促進其分化,使一部分人傾向革命。1925年6月,周恩來在東征回師途中講演時指出,軍隊是工具,“壓迫者拿這工具去壓迫人”,被壓迫階級“也可利用這工具去反抗他們的壓迫者,推翻壓迫者的勢力”;就打倒帝國主義和封建軍閥而言,“軍隊便是實現我們理論的先鋒!”
黨也初步認識到武裝工農的重要性。省港大罷工開始后,共產黨人看到工人糾察隊在鞏固廣東革命根據地的斗爭中所起的重要作用,認為它是中華民族反帝國主義的先鋒隊。1925年10月,中共中央執委會擴大會議討論了武裝工人階級的問題,提出要“有組織的去預備武裝工人階級中最勇敢忠實的分子”。中國共產黨關于中國革命的基本思想初步構成,這就是:無產階級領導農民及其他小資產階級,爭取部分民族資產階級,進行反對帝國主義、反對封建主義的民主革命斗爭,推翻以軍閥政權為代表的帝國主義和大買辦、大地主階級的反動統治,建立各革命階級的聯合專政;在中國所處的國際國內歷史條件下,民族資產階級企圖領導這個革命達到勝利,建立資產階級專政,是行不通的;這個革命作為世界無產階級革命的一部分,將為中國走向社會主義革命準備條件。這些思想,是當時中國共產黨的許多重要成員分別在各自的探索中提出的,雖然還有不確切、不完備之處,彼此間的認識也不盡一致,然而,它是中國共產黨人努力應用馬克思主義于中國國情的寶貴成果,對于后來新民主主義革命理論的形成,具有重大的首創意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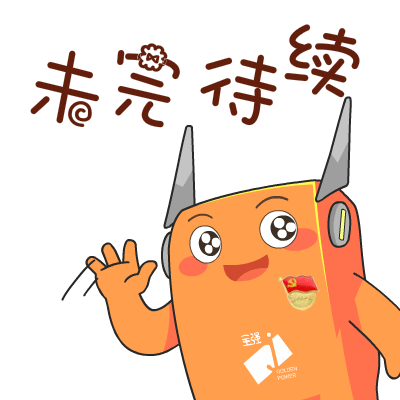
本文資料來源為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出版的《中國共產黨歷史》